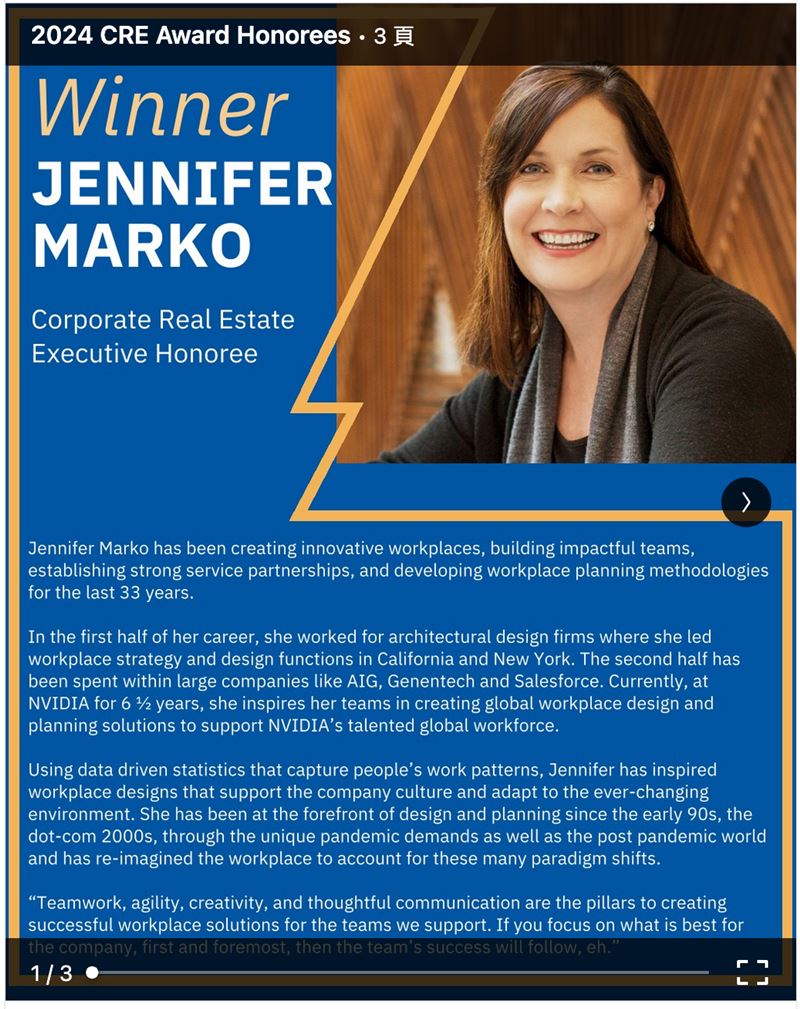財經中心/師瑞德報導

不論台北市政府與新光人壽之間最後協商如何,輝達亞洲區總部落腳台灣應該9成9是可以確定的事情,接下來一個讓更多好奇的問題來了,輝達的總部內部會是誰來設計管理?工作環境如何?有哪些讓普通上班族羨慕到不行的高科技空間呢?
當輝達(NVIDIA)在矽谷持續擴張版圖、從繪圖處理器一路推進到資料中心與生成式AI時,有一位不在台前、卻攸關生產力的關鍵人物,正悄悄改變這家公司的工作場景。2018年加入的 Jennifer Marko,現任輝達全球不動產規劃與職場設計資深總監(Global Senior Director, Real Estate Planning & Workplace Design),她的任務很直接:把黃仁勳對「工程師最能做出人生代表作的職場」的願景,落成在每一座 NVIDIA 辦公場域。
Marko 出身設計世家,父親是設計機場與大使館的建築師,童年輾轉尼泊爾、馬來西亞、印尼、日本與加拿大。這段跨文化背景,如今化為她在輝達主導全球一致、又能在地化的職場語彙:每一個據點都要看得出 NVIDIA 的DNA,但也要融進當地的生活質地。她從東京搬到舊金山,帶著三只行李箱與「用設計改變工作」的野心,在建築與企業端兩邊累積近三十年經驗,先後在 AIG、Genentech、Salesforce 領導職場策略與設計,最後在 NVIDIA「寫下自己的職務說明書」,從零建立設計、規劃與空間管理團隊。
她對「美感」有要求,但更堅持數據先行。團隊長期追蹤會議室使用熱點、峰值時段、動線壓力與工位空置率,再回頭調整配置;在後疫情的混合辦公時代,她主導的 FlexSpace 計畫,取消部分固定座位,導入可預約的 34 吋曲面螢幕工位、個人置物櫃與團隊「鄰里」區,讓不需每週進辦三天以上的人能自由選擇最合適的空間。她說,職場設計不是即興美學,而是建立在「人如何真正使用空間」的證據上。
這套方法論在輝達矽谷總部新大樓 Voyager 身上,被完整演繹。Voyager 是 Endeavor 之後、第二棟量身打造的總部建築,75萬平方英尺、可容納逾3,000人,以三角形量體、中央「山形」綠牆為核心,兩側多層夾層將高活躍的公共區與封閉會議區、臨窗專注工位分帶處理,硬牆會議室被刻意放在「靜」與「動」之間做緩衝,避免協作聲響干擾個人專注。

兩棟建築物之間有一座綠蔭公園相連。公園裡有可開會的座椅區、太陽能棚架遮蔽的露台,甚至設計了「中午散步回報」的自然動線。Marko表示, 「我們希望整個園區就像一個大腦,能快速傳遞想法。」
建物的Pergola(棚架)壓低大尺度空間的感官尺度,長條綠植槽與大面積綠牆則同時改善音場與視覺疲勞。2022年啟用後,數據顯示所謂的「We 空間」,會議、共創、臨時交談,使用率遠超「Me 空間」。即使全棟「We 空間」已達 65%,仍被迅速「吃滿」。這個發現回頭印證了她的判斷:員工進辦公室,是為了目的性協作與靈感交流,不是把家裡的「低頭工作」搬來公司做。
所謂「We Space(We 空間)」與「Me 空間(Me Space)」,是現代辦公設計的重要概念。「Me Space」代表個人專注空間,例如個人辦公桌、隔間、安靜角落,適合需要集中思考、撰寫程式或文件的工作;而「We Space」則是團隊協作區,像開放式會議桌、白板牆、茶水間邊的討論角或沙發區,設計目的是促進交流與創意激盪。
在輝達(NVIDIA)新總部 Voyager,大約 65% 的空間屬於「We Space」。Jennifer Marko 的理念是:員工回到辦公室,不再只是為了「低頭工作」,而是為了「抬頭交流」。她透過數據分析員工動線與使用行為後發現,協作區使用率遠高於個人桌,於是反向設計出以「人際互動」為核心的辦公環境。
這樣的空間設計反映輝達的文化,扁平、透明、速度快。「We Space」讓工程師有更多面對面討論與靈感碰撞的機會;「Me Space」則提供必要的沉澱與專注。兩者共構出一個平衡又靈活的職場生態,成為輝達能持續創新的關鍵基礎。
Voyager 與 2017 年落成的 Endeavor 以公園銜接,綠蔭下的休憩與交流區、加上新的人行橋連接租賃園區,擴大了跨棟互動。Marko 強調,兩棟自有大樓的建築基調都來自黃仁勳的願景,領導層定下的價值,是她與建築師、內部跨功能團隊共筆完成的起點。這也是她在全球擴散設計指南時的原則:不是僵硬的標準,而是一套會隨業務與文化演化、持續敏捷調校的「準則」。導則要求扁平、非階層化的體驗,無論職級,都在開放平面與多元封閉支援空間中工作;並以一致的品牌語言與材質韻律,搭配各地細節的微調,讓班加羅爾、東京或英國辦公室都能「一眼是 NVIDIA、再看是這座城市」。

她同時把「城市尺度的流動」納入園區思考。從 Endeavor 到 Voyager 的行走路徑、樹蔭下的會議角落、被太陽能板遮蔽的戶外協作區,從動線到停留點都服務於 NVIDIA 工程團隊的節奏,快速聚集、集體攻關、再各自拆解。疫情前,輝達提供通勤車、洗車、加油、身心服務與多元餐飲;疫情後,服務按團隊需求動態收縮;回到混合辦公,她把「環境」重新定義為系統,硬體(空間)、軟體(預約與協作工具)與「行為」一起設計,讓人流自然分配到最有效率的節點。
Marko 的目的,從來不是「建築有多震撼」,而是「工程團隊能否更快對齊、更快出成果」。她的團隊在會議室座席、電話間與即時溝通點的比例上不斷實驗;也發現若把開放協作桌硬塞進專注工位區,兩種行為會互相牴觸、導致空間「名義上有、實際上不用」。因此他們寧可用硬牆空間當緩衝,把高活動區與專注區清楚分界,讓不同工作節奏都得到尊重。
走出矽谷,這套文化驅動、數據校準的設計語言正複製到全球據點。班加羅爾新園區 Discovery 的公共空間、亞太與歐洲據點的在地材質與色溫,都在一致與多元間拿捏平衡。她把職場視為「品牌與工程能力的放大器」:當空間能承接 NVIDIA 以團隊為核心、扁平溝通、速度取勝的文化,產出自然會上移。她也把這份工作定義得很簡單:「我們的角色,就是為輝達提供能做出『人生最重要作品』的畫布。」